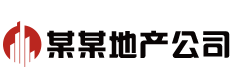放眼苏东坡的评传市场,又有几个作者没有陷在饭圈写作的窠臼中呢?这是最大的奇观所在。
在所有关于苏东坡评传的畅销书中,首先要被提及的是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。该书为英文写作,1947年出版于纽约,1970年在台湾被译为中文,1988年进入大陆市场。
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崇拜,从这本书的原序中可窥一斑:“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,这样守正不阿,这样放任不羁,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……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。”
接下来长篇累牍的修辞,无一不是在传达苏东坡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:“苏东坡的人品,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、广博、诙谐,有高度的智力,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——正如耶稣所说,具有蛇的智慧,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,在苏东坡这些方面,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。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,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,不可多见的。”
即便对于政治这个烂泥塘,苏东坡也“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,但是他却光风霁月,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。他不忮不求,随时随地吟诗作赋,批评臧否,纯然表达心之所感,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,与自己有何利害,则一概置之度外了。”
这不是在写一个人,毋宁说是在塑造一个神了。虽然中国读者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写作风格,但它的普遍性不正说明饭圈写作在历史人物传记领域有多流行吗?
而在所有苏东坡传记中,最畅销的恐怕要算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。但这本书很多地方可以用颠倒黑白来形容。
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为苏轼的苛政洗地。在该书第十章《杭州去来》第二节《吏治》中提到“和买绢”:
近些年来,民间故意织造一种“轻疏糊药”的劣绢,拖到期限迫近,蒙混缴纳,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,习以为风。但是送到京里以后,受配的官吏军人,都说两浙衣赐不好,年有估剥,使原纳专典的职官,被枷锁鞭挞,典卖竭产,还不够赔偿。
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。他命令受纳官吏,必须认真挑选,不受威胁。七月二十七日,受纳场前,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,同时拥入州衙,向知州喧诉。苏轼一面依理晓谕,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,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,要挟官府……
最后苏轼抓了颜章等“首恶”,将他们“法外刺配”(脸上刺了花,充军到远恶州郡去)。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,朝廷无奈,一面诏许苏轼“放(免)罪”,一面将颜章也放了。
李一冰继续写道:“苏轼心里很是不平,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,不成比例,很难做事,上《杭州谢放罪表》……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,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,也深表遗憾……‘临事不能自回’这句话,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、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。”
我先简要说下李一冰未明言的“和买绢”是怎么回事。它最早是所谓“预买绢”:在春天给农民预贷资金,到了秋收时农民再用绢帛还款。但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年代,政府已几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,百姓无偿纳绢,完全变成了一个新税种,又叫“折帛钱”。
北宋是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朝代,士大夫阶层生活非常优渥,底层百姓困苦不堪,赋税之沉重远超明清。苏轼在这个事件中,甚至觉得既有的法律不足以惩戒这些无奈反抗的民众,还要在法外施刑,展现了非常残忍的一面。
用“严别是非、疾恶如仇的勇者”来评价此事件中的苏东坡,是过于没有是非了,但这正契合了饭圈写作的心智。